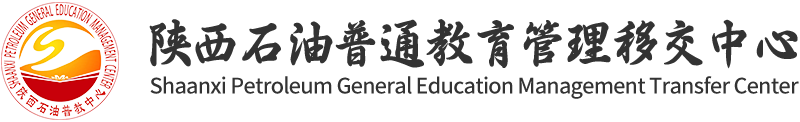年,镌刻在灵魂深处的乡愁
所属分类:党建工作 阅读次数:267 发布时间:2024-11-22
教育管理部 杨笑柳
小时候,对年的期待,超过任何诱惑;对年的感觉,超过任何美好。年,是漫长季节的终点,是满足口欲的起点;年,是孤独枯燥的终点,是热闹悠闲的起点;年,是冰天雪地的终点,是春暖花开的起点……总之,年,是一系列不适的终点,一串串美好的起点。儿时每一个年,都是隆重的,令人神往的。
当季节进入大雪纷飞的时候,就开始期待着过年。到了腊八节,便听到了年的脚步声。这声音,从母亲用刀背砸腊八坨开始。
在物质匮乏的小时候,腊八节的前一天晚上,母亲总要烧一大老碗开水,融入红糖,放在外面窗台上。腊八早晨,母亲把碗倒扣在案板上,诱人的深红色冰块便脱离碗的束缚,这就是腊八坨。母亲用刀背将腊八坨砸成小块,我们姊妹分着吃,甜味混合着冰凉,刺激着味蕾,唤醒了期待了一年的年味。母亲说,腊八坨冻得越实,来年的庄稼越丰收。腊八坨不仅拉快了年的脚步,也是丰收的象征。
到农历“小年”腊月二十三那天,年的脚步声就更急促了。每到这一天,父亲似乎显得格外高兴,总要给我们说一串歌谣,“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去割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;三十晚上熬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
腊月二十三,是我家雷打不动的大扫除,盆盆罐罐,碗筷笊篱,炕上炕下,被子褥子,就连厕所、猪圈也不能遗漏,即使是象征性的,环节必须到位。
此后,便进入到忙碌的准备阶段,家家忙碌,人人忙碌。磨豆腐,蒸馍馍,炸油饼,做发糕,家境好的人家还要杀年猪。家家叮叮当当,热气腾腾,户户高窗的白气从早到晚,竟相外涌。
杀年猪必须赶在立春前,立春前的猪肉存放时间长。如果说杀年猪拉开了过年的序幕,吃杀猪饭则拉开了过年坐夜的序幕。当存放的猪肉挂上了墙,当猪血进了灌肠,接下来便是准备杀猪饭。一锅抄起来掉油的炒肉片,外加几个素菜,不外乎豆腐、白菜、萝卜、土豆,当家家灯火时,便挨家挨户邀请邻居邻亲前来品鲜。就着一年难得的饭菜,喝着农家自酿的烧酒,十里八乡,海阔天空,一年的事故全部集中在饭桌上、酒盅旁。
到了除夕那天,中午的饭要早,和左右邻居比,家家暗暗较劲,你家早,我家比你家还要早。午饭还是臊子面,白面的。那时候,过年最好的饭除了土暖锅,就是臊子面,而土暖锅是正月初二、初三招待亲戚最隆重的美食。午饭后,贴春联,迎门神,这时候,要讲究全家人齐全,男性贴春联,迎门神,女性在锅灶上忙碌年夜饭。
对联贴好了,家务活干完了,还有最后一项最为隆重的仪式:以家族为单位祭祖。于是,各个山头上,出现了一队队上坟的人群。人的多少,代表着家族的兴旺程度。
坐夜,是过年的重头戏,全家人吃着一年难得的美食,聊着一年难忘的事,盘算着来年的生活,谋划着未来的道路。除夕夜,讲究的是必须吃饱,是谓“一夜饱,全年饱”。对于大户人家,或者兄弟多的,每家都要收拾盘子(端几个菜),领上自己的子女,到长辈家里去坐夜,吃着各家的饭,喝着农家的烧酒和黄酒,在昏暗的灯光下,上古传说,邻里琐事,小麦丰收玉米歉收等等,无所不涉。那时候,没有电视,没有网络,没有手机,主要是语言交流。一人说话,大家倾听,偶尔纠正,偶尔补充,没有低头族,只有仰望族,凝神族,倾听族。
坐夜,讲究的是长,越长越好,哪怕到凌晨,到天亮。一家人或几家亲人在一起,其乐融融,全年的辛苦,全年的劳累,全年的委屈,在这一夜得到了充分释放。如果说过年是为了团聚,为了庆祝,为了充分休息,那么,坐夜,则有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作用,是新动力的加油机、助推剂。
儿时的年,是味觉的补给站,是心灵的驿站,是精神的加油站,是传统文化的接力站。如今回想起来,成了镌刻在灵魂深处的乡愁。
(本文转发自2024年2月8日“学习强国”西安学习平台)